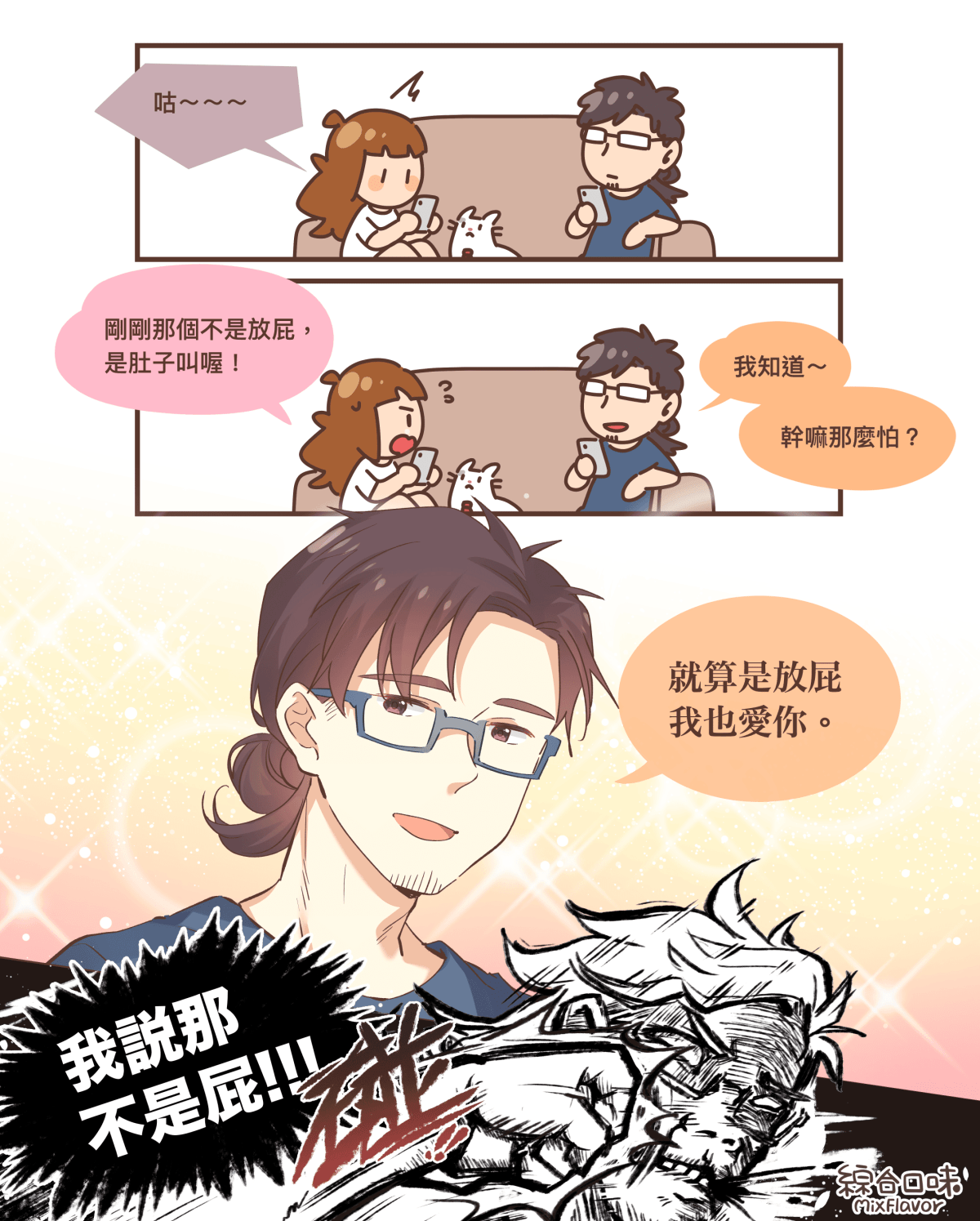今天第一站是Hank的學校Emmaus。去學校時遇到職員,問起制服的事情,她才說今天就要穿(因為大家都穿制服,那妳昨天為何不說?!帛琉人啊~)。於是開始試穿舊生的衣服,昊翰不肯穿,於是職員提議帶他先進教室看到大家都穿制服,HANK就會想穿了吧。
想不到,Hank根本不想進教室。我拉著他,他頭快垂到地上去了。我問他怎麼了,他說:「我害羞啊~」。怎麼樣都不肯進去。只好先去試穿衣服。這時把爸爸叫來,小弟也跟著來了,他才肯穿上制服,隨著爸爸的指令,帥氣拍照。


只是,當進教室時,又是一場拉鋸戰。奇怪的是,一開始兩個老師就只是坐在那裏看著。另一名老師問職員昊翰的名字(昨天沒交接?)。我硬是抱著Hank想讓他坐在兩個男生中間,他依然手讓我拉著,但頭垂到地上,頑強抵抗。
我喊了在門口拍照的小花進來,希望他能幫上忙,但仍毫無用處。此時,一個臉色凶狠的老師終於站起身走了過來,對我們說:「你們先走吧~」於是我和小花對著Hank說:「我們中午就來接你囉~」然後就要離開。Hank此時死命抓住我的裙子,凶狠老師抱起他,他開始哭。職員對著我們說:「心聲都是如此」,我不放心地又問一次,真的嗎?想起在台灣的經驗,於是兩個人匆忙離去,耳邊與腦海迴盪的盡是孩子的哭喊。

其實,Hank與Woody在台灣早就在上學。Hank從小給阿媽帶,中間有一個月去保母家,後因保母超收,從回阿媽懷抱。剛好大舅媽此時出現,也就拜託大舅媽照顧。滿三歲就去讀幼稚園,頭三天都是我陪,之後越讀越快樂,三個月後出國壯遊。Woody的就學史更早,早上兩個多月就已經進入公托中心,直到1歲10個月才因出國離開。
即便如此,在異國陌生的語言環境與人事物之下,這兩位先生還是無法立刻進入交朋友模式。分離焦慮讓他們的淚腺發達,連帶使得在飯店的我的心也空洞洞地。開始質疑自己的決定。
他們的爸爸倒是好整以暇,完全不為所動,並且交代我:「這種時候就應該放下就走,停越久哭越久」。旁邊的大哥也頻頻稱是,說起當年他也是如何把小孩放下就走。還有位大哥安慰我,他的孩子打從出生起沒跟父母睡在一起過一天。旁邊的大姊則說:「我女兒那時哭得更慘!我車開走時,她還在後面追呢~實在想哭」女人們想像著情節糾結著孩子的情緒,男人們認為要放手瀟灑地繼續成人的世界。
我當然屬於女人這一群。
想到我的孩子,在陌生的環境,淚水迸發,喊著爸爸媽媽,我就痛。那想像的畫面如此清晰,彷彿近在眼前。可是,孩子,我寧願你在我面前哭。在我面前,我能懂你哭的原因,決定是要同情同理,還是不理不踩為上。在我面前,你的悲傷彷彿是我能掌握的,我不用擔憂害怕是不是有人欺負了你。
都說要放手。
可是,這手放的有沒有道理,放的是不是時候呢?
我開始懷疑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