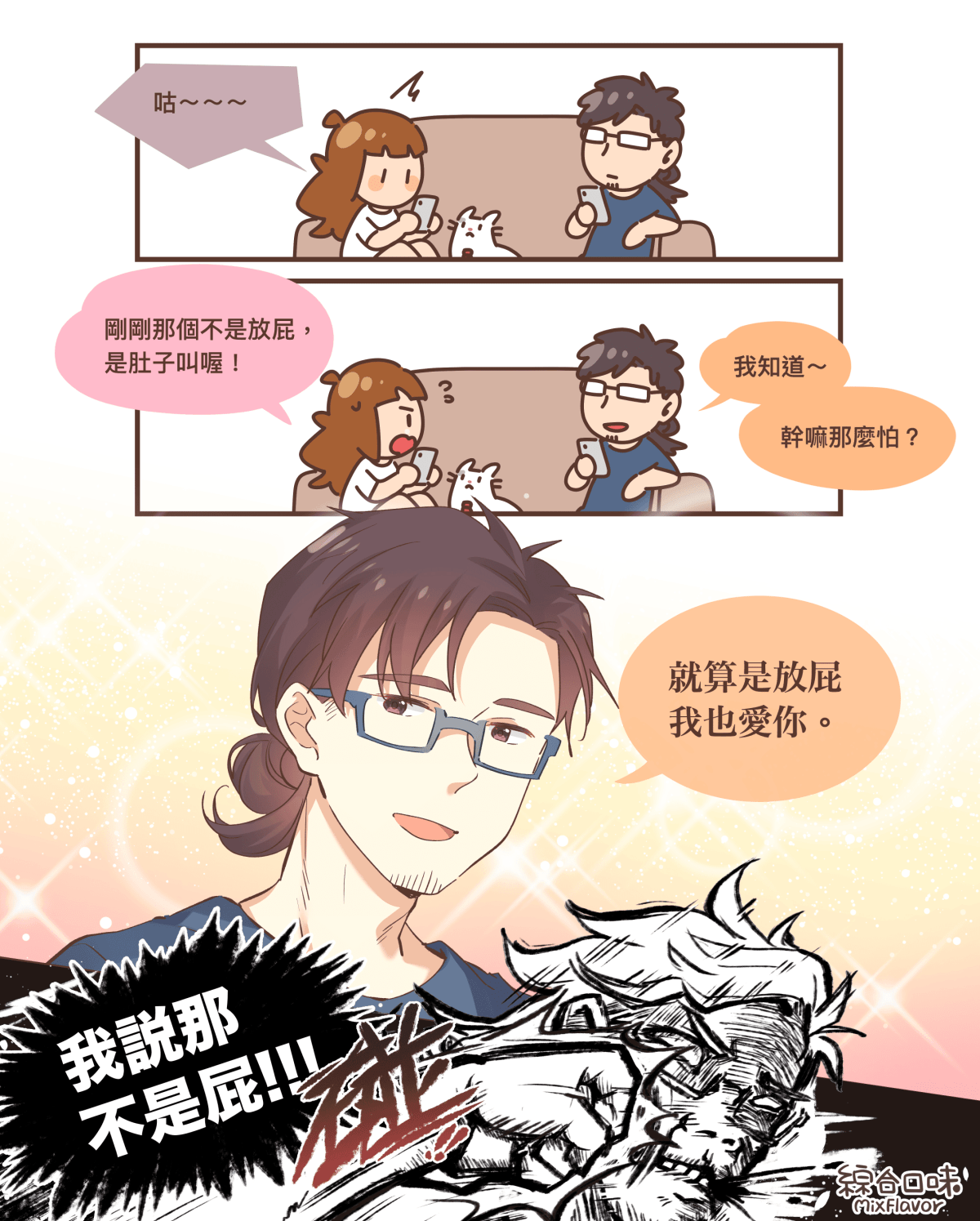第一天送完孩子上學,拎著兩串孩子的哭聲回到車上,我和小花都靜默。奇異地帶點擔憂的空氣在車內流動。但是,中午一到,首先至 Emmaus接Hank,一看到孩子開心的笑容,撲個滿懷,憂慮頓時消散。問Hank學校好玩嗎?「好玩!我有畫畫喔~」內心安定不少。
接著至Belau Child Care Center接Woody。一進教室,原本還在玩的他,看見了爸爸,立馬放聲大哭。 彷彿泣訴他的委屈,直指我們的心狠手辣,拋棄他在這裡。但問老師Woody的表現,老師說很好,只哭了一會兒,就跟同學玩了。問Woody在學校玩甚麼?他燦爛地說:鱷魚~~。
第二天早上,由於有前一晚的心理建設,以及新手錶的誘惑,只要他願意走進教室坐下來,我們就為他戴上新手錶。因此,在我們離開時,他勇敢地說了再見,並沒有哭。直到我從學校辦公室付完錢出來,他的哭聲又開始硬生生穿牆而出。據他事後表示,因為有一個女同學先哭了,所以他才哭。不過,中午去接他時,他那自信滿足喜悅的神情,又讓我覺得去上學是對的。當然,Woody一貫地是在見到我們時,以滿腹委屈地哭泣投入我的懷裡。在吃午餐時,和兩人討論學校種種,都能眉開眼笑,讓我對第三天的上學,有了不少信心。

就在這一天即將以美好做為結束時,原本晚上還宣稱喜歡去上學的Hank,在就寢時,告訴我:「我不要去上學。明天是星期四要上學嗎?那星期五也要嗎?為什麼?」我猜有一部分原因是爸爸在工作沒有陪睡,所以想引起注意。但我更清楚,最大的障礙是他對那個環境還是憂慮恐懼。
其實,我真的對老師有點沒信心。不是因為老師是帛琉人,而是因為老師並沒有在孩子哭鬧時積極展現他們的專業與主動性,而且,不論上學放學,鮮少看見老師的笑容,好似因為吸取了孩子們的哭鬧頑皮,讓她們也開心不起來。
但我不想驟下定論,決定再好好觀察。
第三天早上,又要迎接挑戰,不只是孩子的任務,更是父母的。
在車上我再度開始跟Hank複習去學校的流程,並鼓勵他只要不哭,好好跟爸媽說再見,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鞋子。就在我牽著他的手坐下來,帶他看桌上新貼了他的名字,就要離開之際,他的小手緊緊抓住我的手。
我腦海浮現小花交代的:「你不要停留太久,放下就走」。
可是,我怎麼忍心放開你的手呢?你的小手暖暖的,用一種堅定請求的力量握著我。在那一剎挪,我感覺彷彿只要把你的手甩開,你就會崩盤,我就會太狠。其實,當下我很想把你抱走的。但是,在你的人生路上,我豈能這樣任性遇到障礙就把你抱起來跳過去呢?
最後,趁著老師介入,說了一句媽媽中午回來接你的,我順勢放下了Hank的手。在他的淚水盈眶中,帶著他的呼喊離去。
出了教室的門,小花對著我嘀咕:「在幼稚園教書的朋友說,在幼稚園父母停留越久,對小孩越不好。你要放下就走。」
我憤憤留下一句:「那下次你送他進去」
車上的空氣又凝結了。
我不斷問自己:
讓孩子適應幼稚園就只要放下就走嗎?
我又想起詩人紀伯倫在先知一書中對孩子的描述。他形容,孩子就像一支箭,父母則是弓,弓讓箭有個出發時的支點而已,真正決定箭的方向的是,扮演射手的上帝。
我擅自射箭了嗎?抑或這是上帝的旨意?
孩子上學,最大的考驗是父母。我要再堅強。

孩子上學,最大的考驗是父母。我要再堅強。